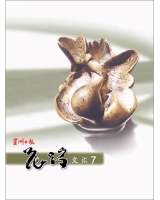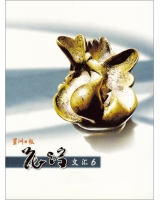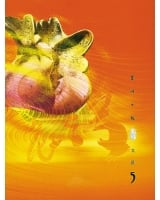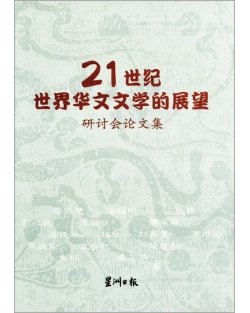 點圖放大 |
|
||||||||||||||||
簡介:
跨進21世紀,星洲日報即給世界華文文壇獻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的宗旨:推動華文文學發展,獎勵優秀作家,樹立藝術典范。兩年一屆,每屆從全球評選一位仍在創作的華文作家,國籍不限,只要以華文創作。
評委會經過費時一年多的推薦、初審、復審、決審的慎密嚴謹的程序,上海作家王安憶以長篇小說《長恨歌》及創作總成就倍受評委肯定,成為首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得獎人。評委之一的陳思和在研討會上稱王安憶為“文學中的異數”。在生活中,王安憶能夠敏銳地感受到不同思潮的興迭,吸收主要的時代訊息,她將它融化在自己的觀念中通過作品呈現出來。她總是在每個思潮即將沒落消褪之前,寫出一部比思潮本身更好的作品來。《長恨歌》擁有她對上海文化的掌握和了解,也有她的理性反思和批判。王安憶得獎,是世界華文文學界眾望所歸。
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頒獎典禮於2001年12月8日在吉隆坡舉行。配合頒獎禮,星洲日報主辦主題為“21世界華文文學的展望”的研討會,在會上發表報告的包括評委和馬新作家。本書收集的是這些作家的論文和相關文章,以及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得獎人王安憶的得獎感言和一些作家對她的作品的評論。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為花蹤文學獎出策出力的海內外作家、學者和文學愛好者。
目錄(部分摘選):
- 當代華文寫作的語言問題——李歐梵
- 對華文文學的三個期望——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的展望——潘耀明
- 文學獎的爭議與執行——世界華文文學領域探討與展望——張錯
- 從陳獨秀的小說觀說起——劉心武
- 本來該有的自信——李銳
- 以后的文學——楊牧
- 華文文學的前景和作家的禪性――劉再復
- 在吉隆坡談小說——王安憶
- 我們如何面對新世紀的文藝?——陳思和
- 臺灣現代詩的朝圣之旅——焦桐
- “世界華文文學”:一個問題――黃子平
內文摘錄:
-
本來該有的自信——李銳
“展望21世紀華文文學”這樣的大題目是最難做的。至少我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學、法文文學或是阿拉伯文文學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結論肯定不會相同。關于文學的發展有很多極為復雜的原因和動力,這被許多理論家分析過,也有過許多不同的結論。在眾說紛紜的原因當中,只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學的發展和一種人為確定的時間界限是無關的。人們對於不同時代文學的劃分,是一種向后看的結果,它最大的理由是為了論述的方便。在用“世紀”劃分年代之前,這個世界上早已經創造出了許多文字和口頭記錄的偉大文學。這些文學都和“世紀”無關。我們使用象形的方塊字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所謂“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數千年里,方塊字的文學發展和“世紀”根本無關。屈原、李白、關漢卿、蒲松齡、曹雪芹們,也都根本沒有“世紀”這樣的時間觀念。可這并不妨礙他們創造出最杰出的文學。
相比之下,華文文學和“世紀”無法避免地互相糾纏在一起的時間不長,從嚴復、林紓的時代算起,總共才一百年多一點。但是,這一百多年是方塊字的文學變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多年里,我們先是被別人用堅船利炮逼著改變自己,接著又用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改變自己。這一百多年,我們幾乎一直是在急于改變自己。于是,我們不但改變了自己的時間觀念,改變了自己的空間觀念,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論理觀念,也改變了自己的審美觀念,我們是從里到外地改變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國”,家園以不再是以前的家園。方塊字的文學也永無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經熟悉的模樣。在這場巨大變化的背后隱藏了一個普通的危機:那就是當空間和時間的概念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時,人們的內心卻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窄,在那個別人給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標準之外,幾乎別無一物。唯一擔心的是自己為什么不像別人?自己為什么不是別人?自己什么樣才能變成別人?這幾乎是一場毫不猶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判家薩義德,把這個過程叫做西方對東方的“東方化”。而我寧愿把外在的殖民、別人的“東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報之邀來到馬來西亞,參加花蹤文學獎的評獎活動,并在檳城、新山等地做過演講。第二年,我發現我在馬來西亞的演講被人引入一場爭論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漢學家提問說,李銳在馬來西亞曾經說過:“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亞更偉大的作家,你同意他這種說法嗎?”提問的人提到的“李銳說過”是一個縮寫和簡化的“說過”。但是報紙上有關的報導我也看過。我記得提到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時候,我的原意是說,他們之中一個是在一場文藝復興運動的大背景下產生,而另一個只是在黑暗中憑著良知做出的孤獨探索。他以一個孤獨者的良知和才華,同樣表達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載的慈悲情懷。他們都寫出了偉大的作品,但是那個孤獨者的探索跟顯得可貴、偉大。在我的講話里并沒有誰比誰“更偉大”這樣的簡單判斷,我說強調的是他們截然不同的歷史處境。在我看來,說李白比杜普更偉大,或者說曹雪芹比莎士比亞更偉大同樣是沒有意義的,那都已經不是以審美的態度來看文學。在這里,報導者或引用者是否簡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談的問題。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準確的判斷,任何一張報紙在做有關報導的時候,都會對事情做一番選擇和簡化,哪怕只是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須縮寫和簡化。我之所以特別在這里引用這個例子,是因為它非常微妙地展現了一種復雜的心態。
如果對馬來西亞華人、華文的歷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我的講話變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亞更偉大”。那是一個長期受到壓抑、歧視、排擠、剝奪的人群,在情感和語言上的直接反抗。這種反抗帶有它充分的道義、情感的合理性,與此同時,卻也附帶了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希望用簡單的否定來填滿那個不平等的深淵。這在所謂發展中國家,在有過被殖民歷史的地區,是一種非常普遍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反過來,這個缺陷立即被簡單地本質化成為“極端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狂熱”等等罪名,變成對所有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指責。所謂“民族主義”的簡單指責,已經成為掩蓋壓迫和剝奪、掩蓋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經成為一切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的“原罪”。而這樣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在所謂發達國家,在有過殖民歷史的國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這樣兩種思維方式來對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亞,引出的爭論必然是如此這般:
“你竟然說曹雪芹比莎士比亞還偉大?你顯然是一個極端種族主義者!顯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義!”
“你說莎士比亞永遠是最偉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范,無非是在頑固地堅持殖民主義的文化立場!顯然是個歐洲中心主義者!”
這樣的互相簡化,離真實和理性越來越遠,離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來越遠。這種理直氣壯的爭論,幾乎是立刻就把文學淹沒在意識形態的政治判斷之中。盡管我知道如今國際流行的文化氣候是“政治正確”,但在我看來,文學要表達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東西,文學要比政治廣闊得多!一個中國母親失去了孩子,和一個英國母親失去了孩子,她們的痛苦是同樣的,這用不著事先選擇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因此,在所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判斷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亞深刻表達的生命悲劇同樣是文學,同樣是偉大的藝術,這才是文學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有不同語種的文學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關于“歐洲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美國文化中心”的判斷都是一種歷史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種為了某種權利和利益而制造出來的神話。我知道,我這樣講文學、文化的平等是一種理想的想象,而理想這種東西幾乎從來就沒有人看到過。在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上,人們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剝奪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別人的壓迫。但是,在所謂的殖民主義、國際壟斷、專制主義之前,偉大的文學不是早已經存在了嗎?在所有的殖民主義、國際壟斷、專制主義橫行的同時,人們不是也一直在創造著偉大的文學和藝術嗎?難道在所謂的“歐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義”之外,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真的就沒有任何另外的意義?被人剝奪、被人壓迫、被人不平等地對待,已經是一種極大的不幸,為什么還要用這種不幸的忿恨去污染文學,為什么還要因為別人的壓迫而詆毀最可貴的生命表達?最可悲的是,為什么還要別人世世代代的剝奪和歧視,內化成自己唯一的判斷尺度?用人世間壓迫、剝奪的尺度,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劃分優劣和等級,豈不是對文學、對人類最大的諷刺?
不錯,古今往來,文學的存在從來就沒有減少過哪怕一絲一毫的人間苦難。可文學的存在卻一直在證明著剝奪、壓迫的殘忍,一直在證明著被苦難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貴,一直在證明著人所帶給自己種種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證明這生命本該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們也許無法預測21世紀的文學走向,但我們卻可以相信文學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這無數努力所得出的結果,不管它是華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馬來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種我們并不熟悉的語言文字所寫成的,它首先應當是我們都深愛的“文學”。這是所有寫作者本來該有的自信。
目前沒有更多圖片。








 購物車
購物車